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
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南宋诗人林升的这首《题临安邸》,短短二十八个字,却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,狠狠刺向了那个偏安一隅、醉生梦死的时代,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千层浪,引得后人不断回味、深思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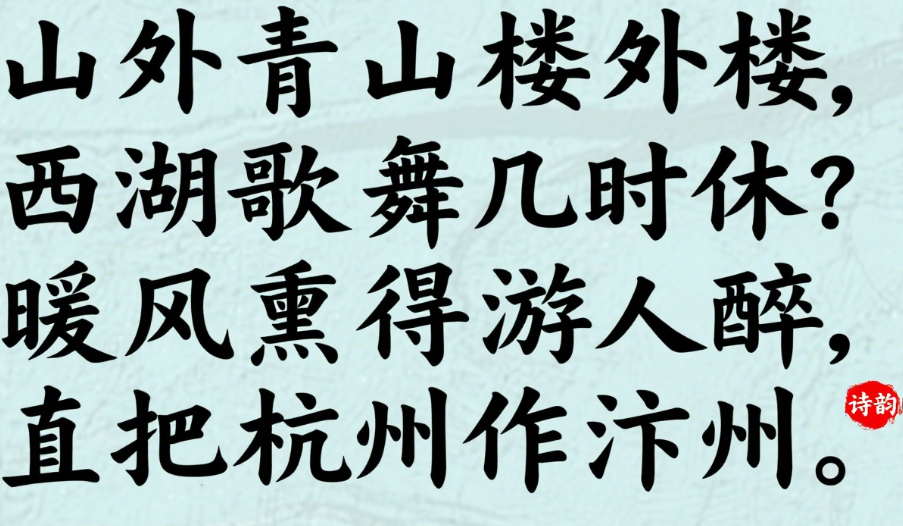
北宋靖康元年(1126 年),是中原大地的一场噩梦。金人如虎狼般凶猛,一举攻陷北宋首都汴梁,宋徽宗、宋钦宗两个皇帝沦为阶下囚,曾经繁华无比的中原国土,尽数被金人侵占。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,山河破碎,百姓流离失所,中原大地哀鸿遍野。赵构在混乱中逃到江南,在临安(今浙江省杭州市)即位,建立了南宋。本以为南宋小朝廷能以北宋亡国为惨痛教训,卧薪尝胆,发愤图强,率领军民北伐中原,收复失地,一雪前耻。可现实却令人痛心疾首,当政者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志向与勇气,他们只想着苟且偏安,为了一时的安稳,对外卑躬屈膝,向金人投降求和;对内,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残酷迫害如岳飞等一心爱国、渴望收复失地的仁人志士。整个朝廷政治上腐败无能,达官显贵们更是放纵自己,一味纵情声色,过着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的生活。就在这样黑暗的社会背景下,林升挥笔写下了这首《题临安邸》,它就像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,倾吐了郁结在广大人民心头的义愤,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。
诗的开篇 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,诗人以极具画面感的笔触,为我们勾勒出临安城的景象。放眼望去,青山连绵起伏,一座接着一座,仿佛没有尽头;楼阁更是鳞次栉比,错落有致地排列着,彰显出这座城市的繁华。这看似是对临安城美丽景色与繁荣景象的赞美,可在这表面繁华的背后,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与悲哀。这些巍峨的楼阁,不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建,而是达官显贵们享乐的场所。诗人看着这一切,心中五味杂陈,他知道,在这繁华的表象下,国家正一步步走向深渊。
紧接着,诗人发出了悲愤的质问:“西湖歌舞几时休?” 西湖,本是杭州的一颗璀璨明珠,自然风光旖旎,景色美不胜收。可如今,这里却成了南宋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天堂。湖面上,游船如织,歌女们轻歌曼舞,丝竹之声不绝于耳,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这无尽的欢乐之中。但林升却无法沉醉其中,他看到的是国家的沉沦,是民族的悲哀。他心中不断地呐喊:这样的歌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?这 “几时休” 三个字,蕴含着诗人对南宋统治者的极度失望与愤怒,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。在这歌舞升平的背后,是无数百姓在沦陷区遭受金人的残酷压迫,是大好河山仍在敌手,可这些统治者却对此视而不见,依旧沉迷于享乐之中。
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 一句,“暖风” 在这里一语双关,既指自然界中那轻柔温暖的春风,让人感到惬意舒适;更暗指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奢靡之风、享乐之风。这股 “暖风”,就像一种无形的毒药,慢慢地侵蚀着人们的心灵。那些 “游人”,并非真正的普通游客,而是特指那些忘了国难,只知苟且偷安、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。他们在这股 “暖风” 的吹拂下,头脑变得昏昏沉沉,如痴如醉,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。“熏” 字和 “醉” 字用得极为精妙,“熏” 字生动地描绘出这股奢靡之风的浓烈程度,就像烟雾一般,弥漫在整个临安城,让人无处可逃;“醉” 字则将那些统治阶级沉迷于享乐、精神麻木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,他们沉醉在这虚假的繁荣与欢乐之中,丧失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。
最后一句 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,堪称全诗的点睛之笔,将诗人的愤怒与批判推向了高潮。汴州,即北宋的都城汴梁(今河南省开封市),曾经是北宋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无比繁华昌盛。可如今,它已被金人占领,沦为了异国他乡。而南宋的这些统治者们,却在临安过着和在汴州时一样的奢靡生活,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,忘记了北方还有无数百姓在盼望着他们收复失地。他们竟然将这临时苟安的杭州,当作了故都汴州,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。诗人用这直白而又犀利的语言,直接戳穿了南宋统治者的丑恶嘴脸,对他们的昏庸无道、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。
林升的《题临安邸》,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诗歌,它更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深刻批判,是对南宋统治者的有力声讨。它以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,通过对临安城景象的描写和对统治者行为的刻画,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民族未来的担忧。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国家危亡之际,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所展现出的担当与勇气。它跨越了时空的界限,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,时刻提醒着我们,要居安思危,珍惜和平,不要被眼前的安逸所迷惑,要始终保持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。
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南宋诗人林升的这首《题临安邸》,短短二十八个字,却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,狠狠刺向了那个偏安一隅、醉生梦死的时代,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千层浪,引得后人不断回味、深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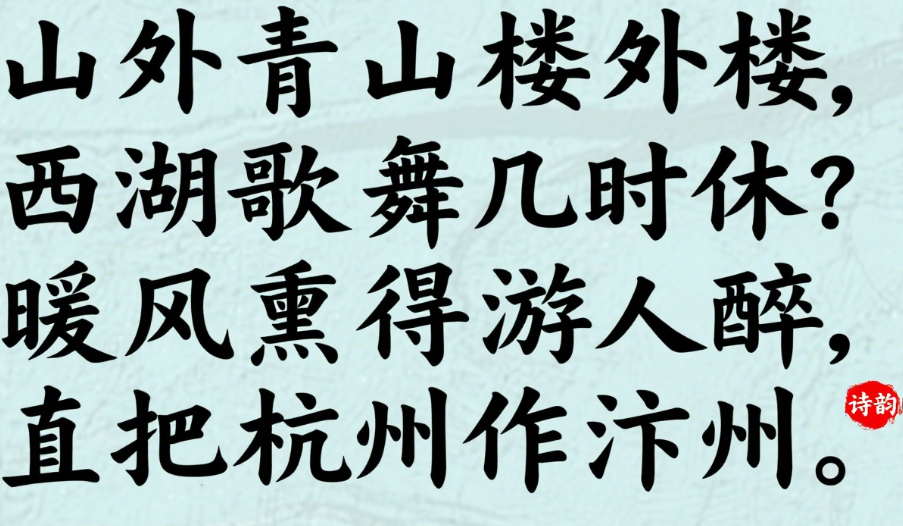
北宋靖康元年(1126 年),是中原大地的一场噩梦。金人如虎狼般凶猛,一举攻陷北宋首都汴梁,宋徽宗、宋钦宗两个皇帝沦为阶下囚,曾经繁华无比的中原国土,尽数被金人侵占。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,山河破碎,百姓流离失所,中原大地哀鸿遍野。赵构在混乱中逃到江南,在临安(今浙江省杭州市)即位,建立了南宋。本以为南宋小朝廷能以北宋亡国为惨痛教训,卧薪尝胆,发愤图强,率领军民北伐中原,收复失地,一雪前耻。可现实却令人痛心疾首,当政者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志向与勇气,他们只想着苟且偏安,为了一时的安稳,对外卑躬屈膝,向金人投降求和;对内,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残酷迫害如岳飞等一心爱国、渴望收复失地的仁人志士。整个朝廷政治上腐败无能,达官显贵们更是放纵自己,一味纵情声色,过着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的生活。就在这样黑暗的社会背景下,林升挥笔写下了这首《题临安邸》,它就像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,倾吐了郁结在广大人民心头的义愤,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。
诗的开篇 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,诗人以极具画面感的笔触,为我们勾勒出临安城的景象。放眼望去,青山连绵起伏,一座接着一座,仿佛没有尽头;楼阁更是鳞次栉比,错落有致地排列着,彰显出这座城市的繁华。这看似是对临安城美丽景色与繁荣景象的赞美,可在这表面繁华的背后,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与悲哀。这些巍峨的楼阁,不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建,而是达官显贵们享乐的场所。诗人看着这一切,心中五味杂陈,他知道,在这繁华的表象下,国家正一步步走向深渊。
紧接着,诗人发出了悲愤的质问:“西湖歌舞几时休?” 西湖,本是杭州的一颗璀璨明珠,自然风光旖旎,景色美不胜收。可如今,这里却成了南宋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天堂。湖面上,游船如织,歌女们轻歌曼舞,丝竹之声不绝于耳,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这无尽的欢乐之中。但林升却无法沉醉其中,他看到的是国家的沉沦,是民族的悲哀。他心中不断地呐喊:这样的歌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?这 “几时休” 三个字,蕴含着诗人对南宋统治者的极度失望与愤怒,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。在这歌舞升平的背后,是无数百姓在沦陷区遭受金人的残酷压迫,是大好河山仍在敌手,可这些统治者却对此视而不见,依旧沉迷于享乐之中。
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 一句,“暖风” 在这里一语双关,既指自然界中那轻柔温暖的春风,让人感到惬意舒适;更暗指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奢靡之风、享乐之风。这股 “暖风”,就像一种无形的毒药,慢慢地侵蚀着人们的心灵。那些 “游人”,并非真正的普通游客,而是特指那些忘了国难,只知苟且偷安、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。他们在这股 “暖风” 的吹拂下,头脑变得昏昏沉沉,如痴如醉,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。“熏” 字和 “醉” 字用得极为精妙,“熏” 字生动地描绘出这股奢靡之风的浓烈程度,就像烟雾一般,弥漫在整个临安城,让人无处可逃;“醉” 字则将那些统治阶级沉迷于享乐、精神麻木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,他们沉醉在这虚假的繁荣与欢乐之中,丧失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。
最后一句 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,堪称全诗的点睛之笔,将诗人的愤怒与批判推向了高潮。汴州,即北宋的都城汴梁(今河南省开封市),曾经是北宋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无比繁华昌盛。可如今,它已被金人占领,沦为了异国他乡。而南宋的这些统治者们,却在临安过着和在汴州时一样的奢靡生活,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,忘记了北方还有无数百姓在盼望着他们收复失地。他们竟然将这临时苟安的杭州,当作了故都汴州,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。诗人用这直白而又犀利的语言,直接戳穿了南宋统治者的丑恶嘴脸,对他们的昏庸无道、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。
林升的《题临安邸》,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诗歌,它更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深刻批判,是对南宋统治者的有力声讨。它以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,通过对临安城景象的描写和对统治者行为的刻画,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民族未来的担忧。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国家危亡之际,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所展现出的担当与勇气。它跨越了时空的界限,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,时刻提醒着我们,要居安思危,珍惜和平,不要被眼前的安逸所迷惑,要始终保持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。
文章评论